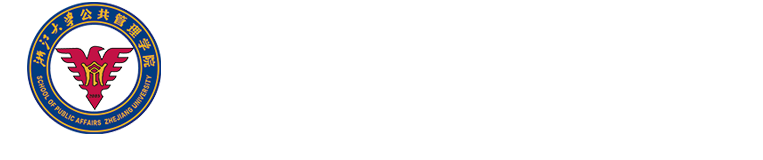原编者按
“三治”是“自治、法治、德治”的简称,“三治融合”的探索目前已进入深水区。
村社书记专职化后,“习惯于依靠行政力量解决问题”,村民的自我调节能力和自治空间受到挤压。
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 南方周末实习生 黄晓颖
责任编辑 | 钱昊平

▲浙江省桐乡市的农村。2013年,桐乡市提出“三治融合”。(人民视觉/图)
“三治融合”基层治理实践走到第十个年头。桐乡市石门镇墅丰村党支部书记窦国勇最直观的感受是,村里的摩擦变少了。
“三治”是“自治、法治、德治”的简称,这是浙江省桐乡市在2013年提出的基层治理模式。
2018年召开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三治融合”经验被定位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精髓:1960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的化解基层矛盾的“枫桥经验”,其核心是“群众的事情群众自己解决”,“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
“三治融合”延续这种基层治理经验,提出“一约两会三团”制度。“一约”即村规民约,“两会”即百姓议事会、乡贤参事会,“三团”即百事服务团、法律服务团、道德评判团,让百姓的事情“自己说了算、自己参与干、自己来评判”。
最早,“三治”中的“德治”排第一,之后是“法治”和“自治”。2017年,参考中共十九大报告的提法,将“自治”放在第一。
“村民自治的规定很多,但墅丰村写在墙上的只有一条。”窦国勇向南方周末记者强调了“自治”的重要性,“就是放权给老百姓”。
2023年8月30日,第四届推进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基层治理学术研讨会(以下简称研讨会)在杭州举办,桐乡市市长王坚在研讨会现场提到,全市一半以上行政村,做到了“连续5年零上访、零诉讼,矛盾零上交”。而“三治”面临的社会环境,也在基层组织架构、治理方式等方面发生着变化。“线上版的‘三治’融合,说实话,也碰到了一些困难。”王坚表示,“我们也在探索,(三治)本身就是在不断迭代、升级的过程之中。”
“‘积分制’只是一个过程”
在墅丰村,保持房前屋后整洁、坚持垃圾分类准确以及参加志愿服务等行为,都能变成积分,违建、酒驾则会导致扣分。一个积分等于一块钱,可以在老年食堂、无人超市兑换物品。
这个看上去有些复杂的积分系统,是为了配合“三治融合”进行的探索。
2013年,桐乡正处于一个“事情越管越多”的时期。时任桐乡市长盛勇军曾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分析,产业的发达带来大量外来人口,而政府的资源和力量有限,如果靠政府“大包大揽”,肯定“管不过来”。
桐乡希望通过社会治理创新提升基层治理水平,“三治融合”试验由此开始。
起初,“三治”分开推行,“德治”在高桥镇试点,“法治”在濮院镇试点,“自治”在梧桐镇试点。一个月后,时任桐乡市委书记卢跃东发现“越搞越不对劲”,三治相辅相成,分开则不行。之后,桐乡将“三治”合一,在高桥镇试点。
2023年8月30日,在研讨会现场,王坚介绍,十年来,桐乡实现平安建设十八连冠,获得浙江省首批二星平安基地,被评为全国乡村治理试点示范县、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
“三治融合”在桐乡取得初步成功后,成为嘉兴全市的基层治理模式,并在浙江省内得到推广,2017年被写进十九大报告。
2020年,桐乡开始在全市推行“三治融合”积分管理制度,依托加、减分清单,以积分量化管理的方式对村民开展考评,并将结果与先进表彰、诚信评价等挂钩,合理进行奖惩。
墅丰村是最早试点推行“三治积分”制度的村之一。“以前很多村民认为,像垃圾分类之类的公共事务,和自己没关系,但有积分制后,参与的热情变高了”,窦国勇说。
墅丰村是纯农业村,村中老人大都在农业基地干活,中午还要回家做饭,“来来回回非常不方便”。窦国勇顺势建立了“老年食堂”,“没有积分的也可以充值吃饭。而想用积分,自然得遵守村规民约,多做点事情”。
但窦国勇想做的不止于此,他的计划是,积分能直接换成钱,还要能在村里实现积分的“内循环”。
钱从哪儿来?窦国勇介绍,“积分”奖励是从村里的补助经费、乡贤资助中出,去年墅丰村在奖励上花了将近10万块。
但在他看来,这笔钱花得值。他给南方周末记者算了一笔账:村里每年雇外人做环保工作要花5万块,如果能够通过积分制里的环保志愿服务解决这一问题,村里就可以将这笔钱花在积分奖励上,不用向外购买服务,“村民也开心”。窦国勇希望2023年能花出去30万。
研讨会现场,提及“三治积分”管理制度,浙江工商大学教授周俊表示,“‘三治积分’制度通过计分的方式,让老百姓在实践中将‘三治’的要求逐渐内化为自身的道德规范,是很有意义的做法”。
但窦国勇也意识到,“‘积分制’只是一个过程”,他认为,“积分制可以根据村中实际情况制定,老的制度甚至可以取消”。
“自治”遇到新挑战
“三治积分”只是“三治融合”众多创新中的一个缩影。被写进十九大报告后,“三治融合”经验开始在全国传开。
据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不完全统计,2018年至2023年6月,桐乡市三治融合馆已经接待除浙江省和上级部门考察调研以外的全国各地政府参访考察团286批次,参访人数达到6977人,其中大部分来自农业农村部门和政法系统。
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河北鹿泉在各村制定村规村约,推出“两会一团”(村情恳谈会、乡贤议事会、道德评判团)模式;重庆市沙坪坝区回龙坝镇聚龙城社区以“和顺茶馆”打造“三治融合”新场景;福建厦门同安区创新探索“邻长制”,将同村相邻的十几户人家划为一个邻区,设立邻长,让居民“有事找邻长”,就地化解纠纷。
“三治融合”何以扩散?在研讨会上,四川大学城乡基层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姜晓萍表示,“‘三治融合’体现了融合共生的治理理念,将自治的民主活力价值、法治的公平正义价值、德治的文明伦理价值融为一体”。她认为,三治融合治理是一个“集成创新”的过程,有参与、有协商、有契约,不仅强调治理,也兼顾了生产、生活、生态的发展。
但经验的扩散并不容易。窦国勇已经接待过不少前来取经的人,他发现,在推广的过程中,“三治融合”难免水土不服。
“有的东西别的地方学不来”,比如经费问题。窦国勇介绍,墅丰村土地流转后,一年流转土地约4500亩,对流转的农户每亩地1100元/年的标准发放租金,部分发展效益农业。他提到,如果北方的农村想要流转土地,一个村内可能有上万亩地,“这么多地,流转出来做什么是一个问题”。
“三治融合”的探索目前已进入深水区。王坚注意到,“群众的诉求更复杂,期待也更高了”,原来单一的民事纠纷,现在转变为民事、经济、行政等多类型相交织的矛盾,部分老百姓希望通过矛盾上交来为自身谋利,加上整体舆论环境的变化,“大事小事,第一时间都在网上扩散”。
“自治”也遇上新的挑战。王坚在发言中提到,村社书记专职化后,“习惯于依靠行政力量解决问题”,村民的自我调节能力和自治空间受到挤压。
浙江工商大学党委书记、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郁建兴是“三治融合”最早的一批研究者,他曾公开指出,“三治”旨在解决基层治理过度行政化问题,“搞村民自治,党委政府还是应该更多还权于民。同时通过法治这个底线和德治这个高线,实现高质量高水平的自治”。
王坚介绍,目前桐乡也在组织体系、优化载体建设和强化数字支撑等方面继续探索。在形式上,针对企业高度集聚的重要场所,设立联动中心。桐乡各地也都有不同探索,“比如高桥街道,聚焦基层的普法,设立‘三治茶座’。凤鸣街道发挥退休村支书的作用,建立老王平安工作室。”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研讨会上,中国社会治理研究会与浙江省公共管理学会还共同发布了“新时代基层治理三治融合建设指南”国家团体标准,该标准在管理内容、建设内容、应用场景、积分管理数字平台等方面为“三治融合”经验的推广提供了规范指引。
郁建兴认为,“三治融合”为当代中国重构基层社会提供了可能性和可行路径。他强调,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是当今中国基层治理中一以贯之的逻辑与原则,未来要将流变的原则嵌入到对“三治融合”的讨论之中,实现基层治理充满活力和稳定有序的双重目标。
本文来源于《南方周末》,2023年9月7日。
乡村振兴培训、社会治理培训、城市管理培训、履职能力培训、应急管理培训、社会保障系统培训、高校培训、两新培训、生态文明培训、市场监督培训、纪检监察培训、农业农村培训、创新创业培训、非公企业、高校改革培训、三农培训、自然资源培训、县域经济培训、国土培训、长三角一体化、城乡协调发展、碳达峰碳中和、大数据、民营经济培训、医保培训、社保培训、国土空间培训、军人事务培训、能源培训等。
涉及培训系统有:
司法系统、教育系统、公安系统、财政系统、检察院、档案系统、工商联、卫健委、宣传系统、城管局、审计系统、档案系统、民宗委、人社局、管委会、编办系统、协会、网信办、文广旅游局、住建系统、卫健系统、医疗系统、金融系统、银行系统培训、城市管理、财税系统、地铁系统、电力系统等。